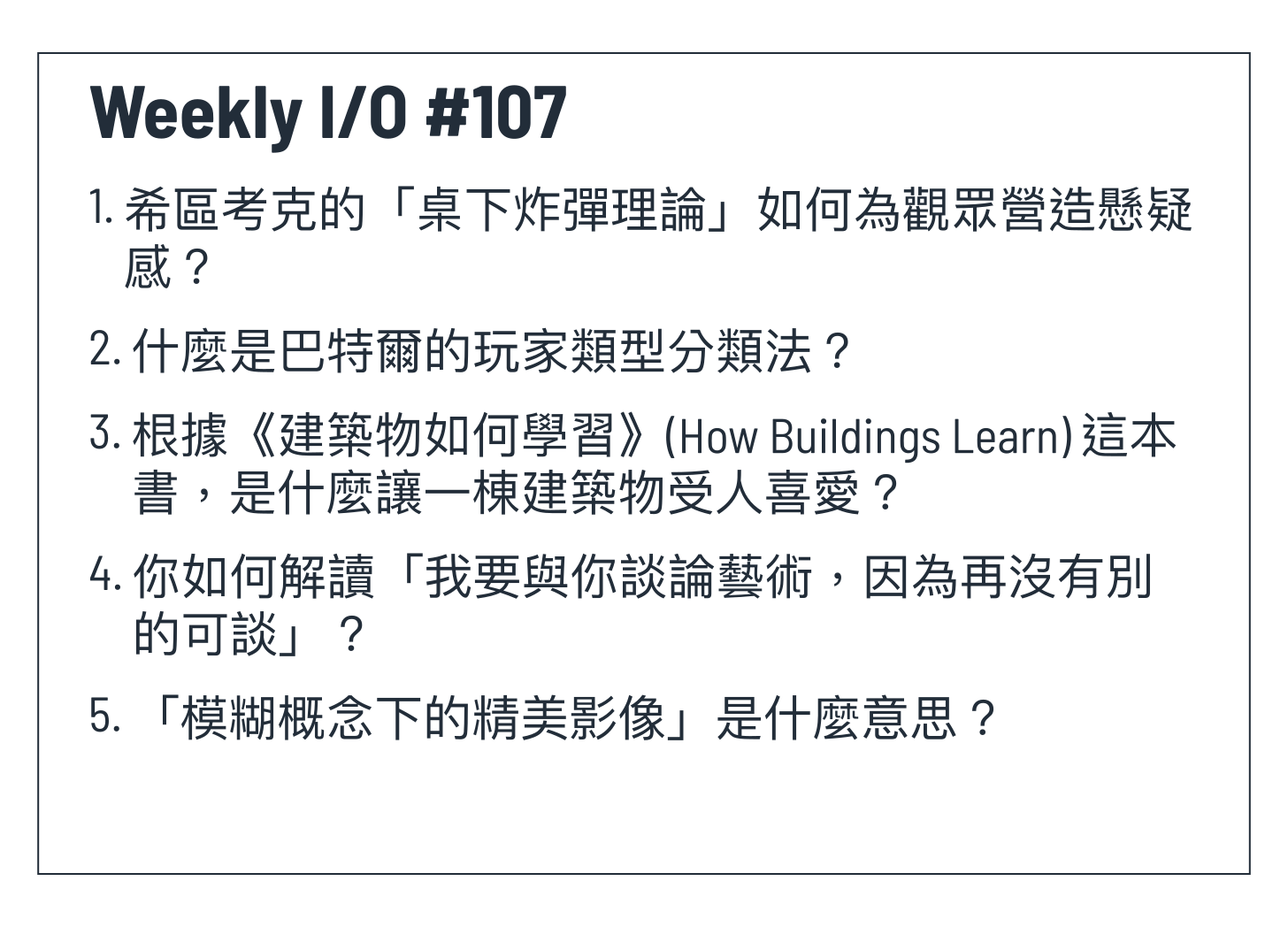桌下的炸彈、人為何玩遊戲、建築物為何會受人喜愛
Weekly I/O #107:桌下炸彈理論、巴特爾玩家分類法、建築的年歲與適應性、藝術的共業、模糊概念下的完美影像
如果你錯過了上次的更新,Weekly I/O 現在有中文版了!如果你是付費訂閱戶,未來所有中文翻譯你都可以直接免費收到。只要回覆這封信,我就會把你加入名單。
現在升級訂閱,你也可以同時收到中、英文版。希望這對你有幫助!
嗨,朋友們,
以下是我這週學到的一些有趣事物:
Malleable software: Restoring user agency in a world of locked-down apps
35 years of product design wisdom from Apple, Disney, Pinterest, and beyond | Bob Baxley
McFly's Movie House: Mastering Film Suspense with Hitchcock’s Bomb Theory
這週我也在嘗試一些新的視覺呈現,歡迎讓我知道你的想法!
輸入
這是我這週學到的東西。
1. 桌下炸彈理論:如果你想讓觀眾深深投入並持續被吸引,創造 15 分鐘的懸疑,而不是 15 秒的驚嚇。透過戲劇性反諷來建立張力,並利用觀眾和角色之間的資訊不對稱。
Podcast:McFly's Movie House: Mastering Film Suspense with Hitchcock’s Bomb Theory
兩個人坐在桌邊交談。如果一顆炸彈在沒有任何預警下突然爆炸,觀眾會感到震驚。這是驚嚇,短暫而強烈。
但如果觀眾看到有人在桌下放了炸彈,並注意到炸彈設定在 15 分鐘後引爆,而角色們卻毫無察覺地聊著天。同樣的對話會變得令人坐立難安。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,張力不斷升高。這就是懸疑。
被譽為懸疑大師的希區考克 (Alfred Hitchcock) 將此稱為「桌下炸彈」理論。給予觀眾更多資訊可以創造更深的情感投入。他稱之為「15 秒的驚嚇」與「15 分鐘的懸疑」之間的區別。
懸疑是透過「戲劇性反諷」建立的,這是一種文學手法,利用觀眾所知道的與角色所不知道的資訊差距。觀眾知道得更多,等待得更久,感受到的張力也更深。
因此,如果你想讓觀眾深深投入並持續被吸引,就要提早讓他們知道危險的存在。讓他們「等待」爆炸的發生。
庫里肖夫效應 (Kuleshov Effect) 是電影製作人使用的另一種認知現象,這是我在 I/O #60 從希區考克那裡學到的。
2. 巴特爾玩家分類法,透過玩家與遊戲元素的互動方式(行動/互動)以及他們的專注點(世界/玩家),來剖析玩家的動機。遊戲設計師應該為成就者創造目標、為探索者設計秘密、為社交家提供聊天工具、為殺手建構競爭舞台。
論文:HEARTS, CLUBS, DIAMONDS, SPADES: PLAYERS WHO SUIT MUDS
問任何玩遊戲的人為什麼玩,他們的回答很可能都是為了好玩。
但人們在遊戲中覺得什麼好玩呢?
遊戲研究員兼教授理查·巴特爾 (Richard Bartle) 在他 1996 年的論文中,提出了一個分類法,用兩個軸線來剖析不同玩家覺得有趣的地方:
行動/互動 (Act/Interact):玩家偏好如何與遊戲元素互動?行動意味著直接控制並將你的意志強加於遊戲或他人身上;而互動則是參與雙向的交流,如連結、合作、探索或社交。
世界/玩家 (World/Players):玩家將注意力集中在哪裡?世界指的是遊戲的環境,包括規則、傳說、系統和任務。另一方面,玩家則代表著人際互動,例如你如何與其他玩家連結或影響他們。
因此,當你結合這兩個軸線時,你會得到四種截然不同的類型:
成就者 (Achievers) (行動 + 世界): 這類玩家喜歡對遊戲世界採取行動,通常為了獲勝或達成目標而玩。
探索者 (Explorers) (互動 + 世界): 這類玩家喜歡與遊戲世界互動,並享受發現新事物的樂趣。
社交家 (Socializers) (互動 + 玩家): 這類玩家喜歡與其他玩家互動,並花費大量時間聊天。
殺手 (Killers) (行動 + 玩家): 這類玩家喜歡對其他玩家採取行動,旨在透過霸凌或權謀來競爭並支配他們。
巴特爾分類法對於遊戲設計很有用,可以用來平衡遊戲並滿足不同類型的玩家。例如,為成就者設定目標、為探索者設計秘密、為社交家提供聊天工具、為殺手建構競爭舞台。
根據互動設計基金會 (Interaction Design Foundation) 的說法,大多數玩家是社交家(約 80%),成就者和探索者各佔約 10%,而殺手則非常少(<1%)。然而,這是一個簡化的分佈,因為大多數玩家是混合類型。一個探索者可能喜歡社交聊天,而一個社交家也可能想要一些成就。
另外還有一些更新的分類法,如Yee 的分類法、HEXAD 模型,或新的 3D 玩家類型模型,但巴特爾的四種玩家類型仍然是重要的基礎。
3. 年歲加上適應性,是讓一棟建築物受人喜愛的原因。建築物向它的居住者學習,而居住者也向它學習。
為什麼老舊的建築物儘管不完美,卻常常讓人感到舒適和親切?
建築物就像生物一樣,注定會不斷演變。一棟真正備受珍愛的建築並非完美或靜止不變的。相反地,它訴說著一個與居民共同持續適應和成長的故事。
年歲(Age)增添了魅力。無論是磨損的磚塊、拋光的階梯,還是褪色的油漆,時間的痕跡都讓我們對一棟建築的過去感到好奇。這樣的結構經得起短暫潮流的考驗,變得更永恆、更貼近人心。
適應性(Adaptation )是另一個關鍵要素。人們不斷地調整建築物以適應他們的生活。他們增建房間、更新廚房,或將舊工廠改造成時髦的公寓。這些改變反映了實際需求和創意表現。
年歲和適應性加深了建築與居住者之間的連結。
麻省理工學院的 20 號大樓 (MIT's Building 20) 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。它雖然簡陋,卻備受喜愛。它的不完美讓使用者能以非傳統的方式改造空間。這樣的建築教導人們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和工作,塑造他們的習慣、日常和認同。反過來,居住者也透過微小的修改,不斷地塑造著這棟建築。
最終,建築與其居住者之間的這種互惠關係,創造了一種持久的情感連結。這就是為什麼能夠適應、日漸老舊的建築,往往比完美、靜止不變的建築更像一個「家」,而建築設計應該創造具適應性的空間,而不是試圖完美預測並為未來的需求進行設計。
這也讓我想起當更多人將一種語言作為第二語言學習時,語言是如何演變的,以及伴隨個體苦難的演化成功。